 |
佛陀信仰的社会形式及其关怀
——以浙、闽地区佛教徒的宗教生活现状为中心
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 主任 李 向
平 教授
出于了解中国宗教与社会变迁的现实关联的目的,本课题以浙、闽地区佛教徒的宗教生活为中心,进行实地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对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力图从现实生活整体上去了解当代佛教徒的基本生活情况。本研究报告即是其调研结果之一。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浙江的杭州、宁波以及福建的莆田、厦门进行,因为这里是我国东南沿海佛教分布的重要地区。
调查中的所得样本为321个,其中浙江杭州72人(占总体的22.4%)、宁波为66人(20.6%)、福建莆田为123人(38.3%)、厦门为60人(18.7%)。
样本的基本情况是:在调查总体中,男性占76.5%(241人),女性占23.5%(74人);在教徒年龄结构方面,17岁以下的年轻教徒为1.5%(5人),18—35岁的青年教徒占43.9%(145人),是教徒中的主体,36—50岁的教徒占22.2%(76人),51—60岁的教徒为12.3%(42人),61岁以上的老年教徒为18.1%(62人);在教徒的职业构成中,学生教徒为35.2%,是教徒的主体,然后依次是工人(16.4%)、农民(6.6%)、教师(5.9%)、公务员(4.9%)、私营雇员(3.0%)、私营管理人员(1.0%)和军人(0.7%),此外还有其他职业(26.3%);教徒的文化结构,没读过书的文盲为1.6%、小学文化为11.4%、中学文化的为42.2%、大中专文化为30.1%、本科学历为9.5%以及研究生学历为5.2%,教徒的文化水平的中位数为中学文化;婚姻状况,教徒中已婚的占30.7%,未婚的占65.9%,而再婚的仅为3.4%。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希望能够看出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形式及其意义体现的可能。需要说明的是,该样本的选择是非随机抽样,因此,此调查结果只能说明调查样本的总体情况。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次调查中的显著性水平p值为0.05。
一、佛教信仰的基本情况
对于每一个佛教徒来说,信佛的基本情况包括他们信佛的时间长短、皈依证是否领取及信佛的原因等。可以认为,如何信仰佛教的基本情况反映了一个佛教徒礼佛的基本心态。
1.信佛的时间
信佛时间是指教徒对佛教产生兴趣并且最终皈依佛教的心路里程。由于在样本中的年龄构成相对较轻,因此,这些信徒信仰佛教的时间都比较短,最多的是在10年以下(62.3%),然后依次是10—15年(20.9%)、16—20年(12.7%),信佛时间在20年以上的仅为5.1%。
调查数据显示,在不同的调查地区,教徒的信佛时间也有差别。
表1:信佛时间与调查地点(n=315)
|
信佛时间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10年以下 |
72.2 |
59.1 |
83.7 |
91.7 |
|
11—15年以下 |
4.2 |
13.6 |
6.5 |
5.0 |
|
16—20年以下 |
13.9 |
21.2 |
7.3 |
1.7 |
|
20年以上 |
9.7 |
6.1 |
2.4 |
1.7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地教徒的信佛时间基本上都在10年之内,但是与福建的莆田和厦门相比,浙江杭州与宁波两地佛教徒的信佛时间都比较长,表现在10年以下的比例均比较低,而在10年以上的每个时间段的比例都比较高。究其原因,可能是佛教在两地发展的时间存在差异。
同时,在信教时间上,应当存在着一个自然年龄的影响。一般来说,自然年龄越大,信佛的时间也越长。其中,当然也不排除由于入教时间较晚所产生的人为的差异,如同表2所表示的那样。
表2:信佛时间与自然年龄(n=313)
|
信佛时间 |
年龄 |
||||
|
17岁以下 |
18—35岁 |
36—50岁 |
51—60岁 |
61岁以上 |
|
|
10年以下 |
100.0 |
85.4 |
53.1 |
60.6 |
59.4 |
|
11—15年 |
.0 |
7.8 |
12.5 |
3.0 |
6.3 |
|
16—20年 |
.0 |
5.9 |
25.0 |
21.2 |
18.8 |
|
20年以上 |
.0 |
1.0 |
9.4 |
15.2 |
15.6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与此同时,教徒的婚姻状况对于个人信仰佛教的时间也有着明显的影响。
表3:信佛时间与婚姻状况(n=305)
|
信佛时间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未婚 |
再婚 |
|
|
10年以下 |
68.9 |
82.9 |
40.0 |
|
11—15年 |
6.7 |
7.8 |
20.0 |
|
16—20年 |
18.9 |
6.7 |
20.0 |
|
20年以上 |
5.6 |
2.6 |
20.0 |
|
|
100.0 |
100.0 |
100.0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基本上信佛时间都在10年以下,但未婚教徒的信佛时间在10年以下(82.9%)的比例最高,而在10年以上的三个年龄段中,再婚教徒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两类教徒。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信佛时间的早晚可能与婚姻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再婚的年龄一般偏大,所以,佛教信仰的时间与年龄的因素发生了特殊的关联;也许是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人们的人生经历对于佛教信仰容易产生亲和力量。所以,个人的年龄如果要影响个人的佛教信仰及其选择,大都是通过婚姻来施加影响的。
2.皈依佛门及其皈依手续问题
皈依证的领取,可以说是佛教徒真正皈依佛门的有形的证明,也可以看作是佛教徒宗教信仰合法性的表证。这对于佛教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佛教徒中,领取过皈依证的占80.1%,而没有领过皈依证的却占到了19.9%。说明相当一部分佛教徒还没有获得整真正合法的身份。
从调查中看,不同地区的佛教徒领取皈依证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表4:皈依证的领取与调查地区(n=306)
|
是否领取皈依证 |
调查地区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是 |
95.6 |
70.3 |
79.8 |
72.7 |
|
否 |
4.4 |
29.7 |
20.2 |
27.3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可以看出,在杭州地区的佛教徒中,信徒们领取皈依证的比例最高,为95.6%,但在同一省的宁波,其皈依证的领取率却最低,仅为70.3%。莆田与厦门的皈依证领取率处在中间,相对较为平均。
在皈依证的领取方面,也与调查对象的年龄有密切的关系。
表5:皈依证的领取与年龄(n=298)
|
是否领取皈依证 |
年龄 |
||||
|
17岁以下 |
18—35岁 |
36—50岁 |
51—60岁 |
61岁以上 |
|
|
是 |
88.9 |
71.9 |
87.1 |
96.8 |
100.0 |
|
否 |
11.1 |
28.1 |
12.9 |
3.2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教徒年龄的增长,领取皈依证的比例也在逐步上升,到61岁以上更是达到100%。这一组数据说明了,年龄越大的教徒,其佛教信仰的形式越是讲究,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皈依佛教的时间都比较早,因此在对待信仰问题方面做得比较规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信徒的文化程度在此方面的作用或影响却是反向的。
表6:皈依证的领取与文化程度(n=292)
|
是否领取皈依证 |
文化程度 |
|||||
|
没读过书 |
小学 |
中学 |
大中专 |
大学 |
研究生 |
|
|
是 |
80.0 |
90.3 |
79.2 |
82.2 |
82.8 |
33.3 |
|
否 |
20.0 |
9.7 |
20.8 |
17.8 |
17.2 |
66.7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文化程度高的佛教徒反而领取在皈依证方面的比例较低,如研究生教徒的不领取皈依证的比率达到了66.7%,而大中专以及大学文化的教徒的不领取率也在17%以上。与此相应成趣的是,在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教徒中,皈依证领取率反而较高,在小学文化的教徒中,领取率高达90.3%。这种巨大的反差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高的教徒,更加注重追求个性化的信仰,更愿意用一种比较随意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信仰,对于领取皈依证这种比较形式化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同时,在领取皈依证上,婚姻状况的不同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
表7:领取皈依证与婚姻状况(n=282)
|
是否领取皈依证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未婚 |
再婚 |
|
|
是 |
87.5 |
75.0 |
100.0 |
|
否 |
12.5 |
25.0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过婚姻经历的教徒领取皈依证的比例较高,已婚教徒为87.5%、再婚教徒为100.0%。这组数据说明,已婚或者再婚的信徒对于皈依证最为看重,而未婚教徒由于一般都比较年轻,对于皈依证的领取问题并不重视,或者是觉得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与是否皈依没有关系。
3.个人认信的精神因素
佛教教义之中注重个人的精神觉悟,讲究信仰的境界,超越世间万事皆苦的约束,这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精神困惑的人们应当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教徒们最初接触佛教的原因,主要是“寻求解脱和觉悟”(62.3%),其次依次是“健康原因”和“求平安”(同为8.3%)、学习或工作压力(6.5%)、个人情感原因(4.2%)、家庭矛盾(3.3%),等等。佛教的目的在于超脱尘世、需求觉悟,这一点已经成为众多佛教徒皈依佛门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社会之中,人们面临的问题多种多样,虽然教徒入教是为了处理尘世间的种种痛苦,但是,为了身体健康、解除工作学习压力、解决家庭矛盾等等世俗问题而入教的也大有人在。
作为教徒接触佛教的主要途径,阅读佛经(39.9%),对于人们信仰佛教具有重要的影响。佛教的书籍及其思想对于人们的精神路向还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同时,除了自身因素以外,佛教徒的信教趋向还要受到血亲影响(36.1%)的影响。血亲作为教徒本人朝夕相处的人群,其行动、思想价值观对于他们无疑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其次,影响教徒本人的最初信仰选择的还有朋友(17.7%)和配偶(2.5%)。在他们影响教徒的作用过程中,佛教行为具有直观性,因此其影响程度也比较深(14.6%)。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教徒在最初接触佛教时,主要还在于本人的自我选择和周围亲戚朋友的影响。
同样,在教徒接触佛教到在众多的宗教信仰中最终选择佛教的过程中,他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还是竭力通过其他手段加以解决的。从调查中可以看出,45.4%的教徒在信奉佛教以前曾经采用其他方式。
对于是否采用其他手段进行求助,存在着基于调查地点、性别的差异。
表8:是否曾以其他方式求助与调查地点(n=280)
|
是否曾以其他方式求助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是 |
29.3 |
80.0 |
42.3 |
33.9 |
|
否 |
70.7 |
20.0 |
57.7 |
66.1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福建两地,在入教前曾经以其他方式求助的教徒比例都比较低,基本上在30—40%之间,而在浙江的两个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杭州地区的曾经求助率为四个地区中的最低,而宁波的曾经求助率却是四个地区中的最高。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更多地要考虑到佛教在以上地区的影响力。
表9:是否曾以其他方式求助与性别(n=276)
|
是否曾以其他方式求助 |
性别 |
|
|
男 |
女 |
|
|
是 |
49.8 |
29.5 |
|
否 |
50.2 |
68.9 |
|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男性教徒在入教前采用其他方式求助的比例非常高,达到了49.8%,而女性教徒则仅为29.6%,男性教徒的比例几乎为女性教徒的一倍。说明男性教徒在入教前为了解决各种问题,更积极、主动地去采用各种方法,有各种尝试,而女性则显得较为消极。
在采用的各种方式中,最为普遍的对象是阅读“各种宗教书籍”(52.5%),希望宗教书籍的阅读来净化心灵,促使他们从当前的精神困扰中暂时解脱。这些书籍当中,不免包括一些佛教经典,这对他们以后皈依佛教无疑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其次,求助于心理治疗和其他治疗的比例(11.9%)也比较高。这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但它往往只能排解当时的问题,事过境迁,也就不能发挥作用。再次,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徒(10.6%)曾经求助于神签,这种方式功利性很强,虽然与制度性宗教有关联,但往往不具有宗教行为的性质。
同时,有3.8%的人曾经求助于耶稣,信奉了另一种宗教。这些人经历了一个较为剧烈的精神转变过程。当然,也有1.3%的教徒曾经寄托于酗酒或吸毒等不良行为,但是,这种教徒极少,并且他们最终还是为佛教教义所感化,皈依了三宝。
信佛的时间、是否领取皈依证以及信仰佛教的个人认信问题,如果置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背景来加以思考,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现象,也不是有缘则来的佛教信仰的自然表现。这么一组调研的材料,恰好是说明了当代中国佛教发展之中一个相当重要并值得注意的社会特征——那就是当代社会生活之中的佛教信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私人化或者个体化的社会形式。
信佛的时间的短少,表明信仰者的年龄已日趋年轻,信佛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事情,或者已不仅仅是关注死后的事情了。特别是许多信仰者从信佛的精神需求上来看,大多数人是为了“寻求解脱和觉悟”(62.3%),而不仅仅是过去那些功利式的求福祈平安健康的方式与内涵了。针对具体的精神困惑、生活矛盾、有求必应式的信仰方式,已经不是调研对象之中主要的构成部分了。
至于皈依证问题,则可以在另一个层面看出佛教信仰的个人化倾向。因为,“皈依可以被定义为加入一个宗教团体,并且认同自己作为其成员。”([英]凯特·洛文塔尔《宗教心理学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页)但是,这里有两种现象,一是文化程度高的人往往对于皈依证问题不重视,另一是未婚的年轻人对于皈依问题也不太重视,似乎是对于其宗教认同不是很高。这些现象的出现,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入教的手续和态度问题。如果放在一个社会背景之下来思考的话,这应当就是人们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是私人的事情,这是个人的信仰,并不在乎什么宗教组织以及加入这个组织所需要办理的一些手续,甚至是要跟从某个皈依师。在这些问题之中,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之上视宗教为个人的精神消费品,仅为私人事情,而这些事情及其活动仅存于私人领域之中。
还有许多的佛教信徒,在信佛之前曾经有过对于其他宗教的选择。这也说明现代人的认信过程及其形式,日益趋向于自由开放、多元选择,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信徒们最为普遍的现象是阅读佛经以及各种宗教书籍,更是说明了宗教信仰的社会形式,已是越发开明、更具备文化理性的一种精神过程。同时,与此紧密联系的是,这种认信过程已经相当的私人化、个体化。因为,书籍的阅读就是一种极其个人化的先行选择。
可以说,这应当是中国社会变迁落实在社会生活层面的一个深刻痕迹。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社会领域分割,社会性的相互理解,促使个体的社会化具备了新的表现形式,促使私人领域以及相应的个人精神领域渐渐独立。虽然,宗教也不见得完全能够为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意义”,但是,个人的认信过程及其认信的方式的私人化、个人化,从而促使人们对于个人终极意义的追求,多少成为了“私人”的精神需要,促使终极意义的秩序社会化、市场化,出现了现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与此紧密相随的,即是私人精神空间的出现,个人宗教性的出现,并将为当代公民社会的价值建构留下了丰富的场域。传统的中国佛教,也将在此过程之中再度呈现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式。
二、宗教生活与活动
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佛教具有自身所特有的一些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方式;作为佛教徒,其宗教生活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宗教仪式和阅读佛教典籍等方式来加深自己的宗教修养,从而反映出佛教徒的宗教经验及其在日常生活的表现形式。
1.宗教活动
如同基督教的礼拜那样,佛教组织维系佛教与佛教徒之间关系的有效手段,就是在寺院中所组织的佛教礼仪,以增加佛教徒对佛的情感,培养佛教徒的宗教意识。在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去寺院礼佛敬佛的教徒,在时间的安排上比较分散,经常坚持去寺院的教徒并不多,更多的教徒是需要时去(20.7%),表明寺院所举行的佛教礼仪在这些信徒心目之中并不重要。很大一部分教徒是选择某个特殊的日子去进行拜祭,或者是佛教节日去(17.4%),或者是农历的初一、十五才去(14.4%),或者是每年春节去烧香(9.2%),时间不一而足。至于偶尔去(10.6%)和不去(1.4%)的比例都比较小,另外还有26.4%的教徒选择其他方式礼佛。
信徒们参加寺院宗教活动的方式难免一致的特点,导致了信徒去寺院目的的多样化。在调查中,人们去寺院的目的虽然比较复杂,但是普遍的是去寻求佛菩萨保佑(27.5%),这是出于教徒自身信佛的最基本目标,也是人们所刻意追求的。除此之外,人们还将去寺院看作是一种生活习惯(16.5%),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还有出于某些外在的原因,如陪伴家人拜佛(15%)、祭祀亲人(4.8%)、参观游览(3.9%),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人们不再为了单纯的宗教目的去寺院,而是多种动机的综合,表现了相当的随意性。这表明了信徒的宗教活动的个体化、私人性,正好与佛教信仰方式的个人化或私人化相互适应;而寺院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在人们的宗教意识之中以及宗教活动之中的重要性正在改变,佛教寺庙从事宗教活动的单一特征也正在变化之中。
在佛教寺院的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的同时,家庭已经成为人们拜佛的重要空间,说明佛教正在逐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宗教活动的家庭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69.3%的教徒家中设有佛龛,而82.4%的教徒经常在家中拜佛。家中佛龛的出现与发展,将逐步取代寺院在佛教活动中的地位与功能。
在家中是否设有佛龛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基于调查地点、职业与婚姻状况等因素的差异。
表10:家中是否设有佛龛与调查地点(n=280)
|
家中是否设有佛龛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是 |
79.7 |
77.6 |
67.0 |
52.7 |
|
否 |
20.3 |
22.4 |
33.0 |
47.3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杭州与宁波的教徒家中设有佛龛的比例较高,其中,以杭州的教徒比例最高,而福建两地教徒家中设有佛龛的比例较低,其中以厦门的教徒比例最低。由此可以看出,浙江的佛教对教徒日常生活的影响较福建的影响更深。
表11:家中是否设有佛龛与职业(n=266)
|
家中是否设有佛龛 |
职业 |
||||||||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公务员 |
私营雇员 |
私营管理 |
教师 |
学生 |
其他 |
|
|
是 |
85.4 |
66.7 |
100.0 |
78.6 |
37.5 |
.0 |
77.8 |
62.5 |
67.6 |
|
否 |
14.6 |
33.3 |
.0 |
21.4 |
62.5 |
100.0 |
22.2 |
37.5 |
32.4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发现,军人、工人、农民、公务员以及教师、学生等职业的教徒在家中设立佛龛的比例较高,尤其是本次调查中的军人教徒,设立佛龛的比例更是达到100%;与这些职业相比,私营管理人员、私营雇员等职业的教徒在家中设立佛龛的比例比较低,尤其是私营管理人员,不设佛龛的更是达到了100%。一些职业教徒设立佛龛,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做法,而在私营企业的雇员与管理人员这种新兴职业中,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表12:家中是否设有佛龛与婚姻状况(n=280)
|
家中是否设有佛龛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未婚 |
再婚 |
|
|
是 |
79.7 |
63.4 |
75.0 |
|
否 |
20.3 |
36.6 |
25.0 |
|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未婚教徒家中设有佛龛的比例最低,而已婚教徒家中设有佛龛的比例最高。
家中设有佛龛是家中拜佛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在家中拜佛已经成为教徒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不同地区、职业、文化程度与婚姻状况对家中拜佛的影响有助于加深对佛教的社会影响以及对教徒参加宗教活动方式的认识。
表13:是否在家中拜佛与调查地点(n=296)
|
平时在家中是否拜佛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是 |
98.6 |
88.1 |
81.1 |
58.2 |
|
否 |
1.4 |
11.9 |
18.9 |
41.8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浙江地区的佛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例都比较高,其中杭州的比例最高,为98.6%,而福建地区的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例都比较低,而厦门的教徒尤其低,为58.2%。从这可以看出,浙江地区的教徒参与宗教活动的自觉程度比较高。
表14:是否在家中拜佛与职业(n=296)
|
是否在家中拜佛 |
职业 |
||||||||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公务员 |
私营雇员 |
私营管理 |
教师 |
学生 |
其他 |
|
|
是 |
90.0 |
82.4 |
100.0 |
92.3 |
55.6 |
66.7 |
82.4 |
76.8 |
84.7 |
|
否 |
10.0 |
17.6 |
.0 |
7.7 |
44.4 |
33.3 |
11.8 |
23.2 |
15.3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种职业的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例都比较高,其中军人、公务员、工人的比例最高,而在私营雇员与私营管理人员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例虽然不少,但同时不在家中拜佛的比例也比较高,分别为44.4%与33.3%。这种情况也可以看出信徒们的宗教活动的随意性,可能是根据各自的生活习惯而自己决定从事宗教活动的方式。
表15:是否在家中拜佛与文化程度(n=282)
|
是否在家中拜佛 |
文化程度 |
|||||
|
没读过书 |
小学 |
中学 |
大中专 |
大学 |
研究生 |
|
|
是 |
100.0 |
84.8 |
86.4 |
85.5 |
74.1 |
37.5 |
|
否 |
.0 |
15.2 |
13.6 |
14.5 |
25.9 |
62.5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文化程度越高,在家中拜佛的比例则越低,没读过书的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例最高,为100.0%;研究生的比例最低,为37.5%。其中的原因是文化程度越高,就越将佛教看作是一种单纯的个人的宗教信仰,认为是个人的活动,而不局限活动的地点以及参与活动的方式;而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教徒,活动方式也易于程式化、固定化,因此,家中拜佛的比例也就越高。
表16:是否在家中拜佛与婚姻状况(n=272)
|
在家中是否会拜佛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未婚 |
再婚 |
|
|
是 |
92.0 |
77.0 |
90.0 |
|
否 |
8.0 |
23.0 |
10.0 |
|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已婚与再婚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例较高,而未婚教徒的比例都比较低。在婚姻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要比未婚时多许多,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求助佛来解决,因此他们拜佛的比例较高。
从在家中拜佛的比例来看,随着人们学习、工作的日益繁忙,人们已经习惯于有时间就拜(为35.2%),坚持每天一次以上的教徒占29.6%,而每天一次拜佛的教徒占16.5%,同时,与去寺院拜佛想类似,有2.6%的教徒也是需要时才拜。
在家中拜佛的频次上,存在着基于调查地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表17:拜佛频次与调查地区(n=267)
|
拜佛频次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每天一次以上 |
49.3 |
10.0 |
26.7 |
26.7 |
|
每天一次 |
31.0 |
16.0 |
9.9 |
8.9 |
|
有时间就拜 |
9.9 |
72.0 |
40.6 |
22.2 |
|
需要时就拜 |
1.4 |
.0 |
3.0 |
6.7 |
|
其他 |
8.5 |
2.0 |
19.8 |
35.6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调查地区来看,坚持每天一次以上的以杭州的教徒比例最高,为49.3%,而宁波教徒的比例最低(10.0%);每天一次的比例也以杭州的比例最高,为31.0%;而宁波的教徒有时间就拜的比例最高,达到72%,此外,莆田的教徒比例也很高(40.6%),需要时就拜的比例以厦门教徒最高(6.7%),说可以明杭州地区佛教徒的宗教意识更为正常、规范。
表18:拜佛频次与性别(n=262)
|
拜佛频次 |
性别 |
|
|
男 |
女 |
|
|
每天一次以上 |
22.1 |
54.0 |
|
每天一次 |
13.6 |
23.8 |
|
有时间就拜 |
43.2 |
9.5 |
|
需要时才拜 |
3.0 |
1.6 |
|
其他 |
18.1 |
11.1 |
|
|
100.0 |
100.0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女性教徒的拜佛频率要明显高于男性教徒,每天一次以上和每天一次的比例(54.0%和23.8%)均高于男性角度,而男性教徒更倾向于有时间就拜(43.2%)与需要时才拜(3.0%)。可见,在拜佛这个环节上,女性教徒要比男性教徒在宗教生活上更为投入一些。
表19:拜佛频次与年龄(n=259)
|
拜佛频次 |
年龄 |
||||
|
17岁以下 |
18—35岁 |
36—50岁 |
51—60岁 |
61岁以上 |
|
|
每天一次以上 |
14.3 |
22.6 |
25.9 |
53.3 |
54.8 |
|
每天一次 |
42.9 |
9.8 |
29.6 |
20.0 |
32.3 |
|
有时间就拜 |
14.3 |
45.1 |
33.3 |
13.3 |
6.5 |
|
需要时才拜 |
.0 |
3.7 |
.0 |
3.3 |
.0 |
|
其他 |
28.6 |
18.9 |
11.1 |
10.0 |
6.5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徒的拜佛次数也在不断增加。其中,拜佛频率最高的是61岁以上的老年教徒,每天一次以上的比例为54.8%;而17岁以下的教徒的比例也不低,每天一次的比例为42.9%;有时间就拜的比例以18—35岁的教徒最高,为45.1%。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年龄最大与最小的教徒由于空余时间比较多,因此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拜佛,另外老年教徒由于临近晚年,精神上较为孤独,这些因素都可能会促使他们更多地拜佛。
表20:拜佛频次与职业(n=254)
|
拜佛频次 |
职业 |
||||||||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公务员 |
私营雇员 |
私营管理 |
教师 |
学生 |
其他 |
|
|
每天一次以上 |
41.9 |
14.3 |
.0 |
23.1 |
16.7 |
.0 |
25.0 |
26.1 |
35.7 |
|
每天一次 |
23.3 |
7.1 |
100.0 |
7.7 |
50.0 |
100.0 |
31.3 |
10.2 |
12.9 |
|
有时间就拜 |
18.6 |
78.6 |
.0 |
69.2 |
16.7 |
.0 |
37.5 |
36.4 |
30.0 |
|
需要时才拜 |
2.3 |
.0 |
.0 |
.0 |
.0 |
.0 |
.0 |
4.5 |
2.9 |
|
其他 |
14.0 |
.0 |
.0 |
.0 |
16.7 |
.0 |
6.3 |
22.7 |
18.6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工人每天一次以上的比例最高,为41.9%,说明他们的拜佛活动比较频繁;在每天一次拜佛的比例,以军人和私营管理人员最高,均为100%,有时间就拜的比例以农民与公务员比较高,分别为78.6%和69.2%。职业间之所以产生差异,是因为劳动的时间与场所的限制,那些有明确的时间与场地的工作的教徒拜佛的时间较为固定,反之,教徒的拜佛就没有规律了。
表21:拜佛频次与文化程度(n=255)
|
拜佛频次 |
文化程度 |
|||||
|
没读过书 |
小学 |
中学 |
大中专 |
大学 |
研究生 |
|
|
每天一次以上 |
40.0 |
41.9 |
27.2 |
25.0 |
40.0 |
9.1 |
|
每天一次 |
40.0 |
16.1 |
12.6 |
23.8 |
12.0 |
18.2 |
|
有时间就拜 |
.0 |
32.3 |
40.8 |
32.5 |
28.0 |
18.2 |
|
需要时才拜 |
20.0 |
.0 |
3.9 |
.0 |
4.0 |
9.1 |
|
其他 |
.0 |
9.7 |
15.5 |
18.8 |
16.0 |
45.5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文化程度较低的教徒,拜佛的频率也比较高,没读过书的教徒每天一次以上和每天一次的比例都为40%,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教徒,每天拜佛的次数也比较少,表现在大学每天一次为12.0%,每天一次以上的研究生教徒比例为9.1%;而中等文化程度的教徒有时间就拜的比例最高,有时间就拜的比例中学教徒为40.8%。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大学文化的教徒每天一次以上的比例也较高(40%)。说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教徒对于拜佛的态度也逐步趋向理性化,而拜佛的方式及其选择也更是出入个人的生活方便。
表22:拜佛频次与婚姻状况(n=245)
|
拜佛频次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未婚 |
再婚 |
|
|
每天一次以上 |
40.5 |
23.7 |
22.2 |
|
每天一次 |
26.2 |
9.9 |
44.4 |
|
有时间就拜 |
20.2 |
42.8 |
33.3 |
|
需要时才拜 |
1.2 |
3.9 |
.0 |
|
其他 |
11.9 |
19.7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已婚教徒每天一次以上的比例最高,为40.5%,而再婚教徒每天一次的比例最高,为44.4%。未婚教徒有时间就拜的比例和需要时就拜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2.8%和3.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结婚的教徒的拜佛活动更加有规律,而未婚的教徒则无规律。
2.阅读佛经或相关佛教书籍
阅读佛经是佛教徒了解佛教教义、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促使身心不断得到“解脱”的途径之一,因此除了拜佛以外,作为教徒,最重要的机会就是佛经以及相关佛教书籍的阅读。在调查中,很大一部分(77.5%)教徒在平时阅读佛经,不读佛经的教徒仅占1.9%,另有18.4%的教徒偶尔读佛经。由此可以看出,广大教徒已经把佛经的阅读作为一种信仰的方式或者是信仰的表达了。
从调查数据看,阅读佛经的情况因调查地区、样本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表23:阅读佛经与调查地点(n=315)
|
阅读佛经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读 |
100.0 |
42.4 |
84.4 |
75.4 |
|
不读 |
.0 |
6.1 |
.0 |
3.5 |
|
偶尔读 |
.0 |
50.0 |
10.7 |
21.1 |
|
其他 |
.0 |
1.5 |
4.9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杭州的教徒阅读佛经的比例非常高,达到100%;莆田的教徒居其次,为84.4%;厦门的教徒为75.4%,最少的是宁波的教徒,为42.4。不读的比例最高的是宁波(6.1%),偶尔读的比例最高的也是宁波的教徒(50.0%)。说明佛教文化在杭州的影响很深,教徒们主动、积极地阅读佛经;反差最大的是宁波,几乎是四个地区中阅读佛经比例最低的地区。福建的两个地区阅读佛经的比例则位处中间。
表24:阅读佛经与年龄(n=305)
|
阅读佛经 |
年龄 |
||||
|
17岁以下 |
18—35岁 |
36—50岁 |
51—60岁 |
61岁以上 |
|
|
读 |
55.6 |
76.7 |
62.5 |
84.8 |
100.0 |
|
不读 |
11.1 |
1.0 |
6.3 |
3.0 |
.0 |
|
偶尔读 |
11.1 |
20.3 |
31.3 |
12.1 |
.0 |
|
其他 |
22.2 |
2.0 |
.0 |
.0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年龄越大,阅读佛经的比例也就越高。61岁以上的老年教徒经常读佛经的比例最高,为100%,其次是51—60岁的教徒,为84.8%,而17岁以下不读佛经的教徒的比例最高,为11.1%。偶尔读的比例以36—50岁的教徒比例最高,为31.3%。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老年教徒之所以经常阅读佛经,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业余时间较多,也可能是他们的佛教信仰比较虔诚。
表25:阅读佛经与职业(n=299)
|
阅读佛经 |
职业 |
||||||||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公务员 |
私营雇员 |
私营管理 |
教师 |
学生 |
其他 |
|
|
读 |
89.8 |
70.0 |
50.0 |
60.0 |
22.2 |
33.3 |
72.2 |
78.1 |
89.7 |
|
不读 |
.0 |
10.0 |
.0 |
6.7 |
.0 |
.0 |
.0 |
2.9 |
.0 |
|
偶尔读 |
10.2 |
20.0 |
50.0 |
26.7 |
77.8 |
66.7 |
27.8 |
14.3 |
9.0 |
|
其他 |
.0 |
.0 |
.0 |
6.7 |
.0 |
.0 |
.0 |
4.8 |
1.3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 |
从表中我们发现,在各职业的教徒中,不读佛经的比例都比较低,只有农民教徒为10%,有点高。军人教徒经常读和偶尔读的比例相同,同为50%。经常读佛经的教徒中包括工人、学生、教师、农民、公务员等等,而经常读佛经的比例比较低的是私营雇员和私营管理人员教徒。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新兴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的宗教观念更为随意,或者是商业活动的繁忙,因此也就无暇做到经常阅读佛经。
表26:阅读佛经与文化程度(n=301)
|
阅读佛经 |
文化程度 |
|||||
|
没读过书 |
小学 |
中学 |
大中专 |
大学 |
研究生 |
|
|
读 |
100.0 |
94.1 |
78.9 |
72.5 |
85.7 |
40.0 |
|
不读 |
.0 |
.0 |
2.3 |
1.1 |
.0 |
13.3 |
|
偶尔读 |
.0 |
2.9 |
14.8 |
25.3 |
14.3 |
46.7 |
|
其他 |
.0 |
2.9 |
3.9 |
1.1 |
.0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比较反常的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信徒,反而出现经常阅读佛经的比例。没读过书的教徒比例为100%,而研究生教徒的比例仅为40%。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高的教徒,自以为能够了解佛教而不注意阅读佛教的这种信仰方式,因此对佛经的阅读反而不多了。同时,这也可能说明了文化程度较高的信徒,只是把佛教信仰作为他们的精神生活之中的一部分而已,从而并不注重佛教的阅读。
除了阅读佛经以外,作为佛教徒,还应该更多地阅读有关佛教的书籍,以增进对于佛教教义的了解,因此阅读佛教有关的书籍,对于提高教徒的修行非常重要。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阅读其它有关佛教的书籍方面,84.4%的教徒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不读的也只有15.6%。
在这方面,同样也存在着基于调查地点、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表27:阅读相关的佛教书籍与调查地点(n=294)
|
阅读相关佛教书籍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读 |
95.1 |
69.4 |
87.9 |
81.8 |
|
不读 |
4.9 |
30.6 |
12.1 |
18.2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杭州佛教徒阅读相关宗教书籍的比例最高,为95.1%,虽然同在一省,但是宁波的教徒阅读别的佛教书籍的比例在四个地区中却是最低的(69.4%)。而在福建的两个地区,阅读别的佛教书籍的比例都比较高,在80%以上。这种现象要归因于不同地区的佛教影响力的大小。
表28:阅读相关的宗教书籍与职业(n=278)
|
阅读相关宗教书籍 |
职业 |
||||||||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公务员 |
私营雇员 |
私营管理 |
教师 |
学生 |
其他 |
|
|
读 |
82.1 |
57.9 |
100.0 |
80.0 |
88.9 |
100.0 |
94.4 |
81.2 |
94.5 |
|
不读 |
17.9 |
42.1 |
.0 |
20.0 |
11.1 |
.0 |
5.6 |
18.8 |
5.5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军人、私营管理人员、教师、私营雇员、工人、公务员等职业的教徒阅读相关佛教书籍的比例较高,最高的是军人与私营管理人员,均为100%。只有农民阅读别的佛教书籍的比例比较低,可以看出,阅读相关的佛教书籍,已经成为各种职业佛教徒的共同选择;但是农民由于自身的生活视野所限,对相关的佛教书籍接触较少。
上述的田野调查及其相关的几组数据,可以说是基本表明了浙闽地区佛教徒的日常佛教生活及其方式。虽然这些问题大都是围绕着家中是否设立佛龛、礼佛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等、以及阅读佛经或相关佛教书籍,但是,对于问题的处理和态度,却是可以看出佛教信仰与这些佛教徒日常生活的真实关系。
一个基本的却又是普遍的现象就是,信徒的宗教生活及其方式没有一定的规范、时间和地点,过宗教生活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至于职业、年龄、婚姻、地区等社会因素,也无法看出它们对于信徒们宗教生活的普遍的制约和影响。信徒是否去寺院礼佛参加宗教活动,自然也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可以贯彻各个职业或各个社会阶层的佛教生活习惯之中。或者去寺庙,或者在家里,或者是节假日再到寺庙里去进香礼佛,信徒们的宗教行为已经异常“随缘”,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安排自己的宗教生活。
尤其想提出来做些说明的,是那些私营经济的雇员或管理者,基本上不在家里设立佛龛,但是又因其生活习惯而常常不去寺庙参加法会等活动,但又喜欢阅读佛经或佛教书籍,比例几乎是100%。这类佛教信徒近年来已经成为佛教信徒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了。特别是在浙闽地区中经济比较发展的一些乡镇,尤其如此。这一类佛教信徒在乡镇之中往往又是商业精英,所以其影响较大。他们的佛教信仰方式也同时表现出相当的个人随意的特征。还有的就是那些年轻的、文化程度较高的佛教信徒,往往也是方式随意,个人主观的精神色彩非常突出,更加注重自己的信仰需要,而不愿意承受传统习俗、宗教教规的约束。此类现象的不断出现并有持续的逻辑,则会成为那种“信仰但不归属”、“看不见的宗教”、宗教表现出近似于市场的社会特征,由信仰者自己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与此现象紧密联系的是,制度宗教只能留下一个“礼仪宗教”模式的外壳。特别是那些用来连接宗教与社会、考察宗教社会功能及其作用形式的宗教礼仪,在这里也只能是由人自由选择,而无法产生宗教本身所应该具有的约束力量。宗教所与生俱来的威慑力量,也相应的成为的成为了个人的精神感受或心灵体验了。
于是,(个人)信仰与(僧团)宗教发生分离。佛教信仰者作为社会行为的意义层次构成了,但是,另一个是佛教信仰者之间互相配合,并作为佛教团体群体行动的层面,则由此被虚化了、被淡化了。专业的佛教团体与私人的佛教信仰之间的问题出现了,私人信仰与公共寺庙的矛盾关系成型了。这个问题将极大地影响到佛教文化及其道德伦理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关怀形式。
三、佛教信仰经验
宗教对于信徒来说,能为他们提供一种独特的心灵感受,使他们能够感到终极精神的存在并能够与之交流,由此获得信仰经验的完成和满足。如果说佛教能够具有社会关怀的功能的话,最为关键的,是要从佛教徒自身的宗教体验来考察这些佛教徒宗教体验的精神内涵及其社会意义。
1.宗教的重要性
宗教信仰本身会使教徒产生一种宗教体验,促使他们通过接受教义、与宗教中的终极精神相互交流,从而获得一种非常神圣的宗教感受。对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讲,佛教信念中的情感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人生的寄托。
在调查中,当问及“宗教在你的生活中是否重要”时,75.7%的教徒认为非常重要,10.7%的教徒认为有些重要,只有12.3%的教徒认为不太重要,而认为完全不重要的教徒更少,只占调查样本总体的1.3%。
表29:宗教重要性与调查地点(n=309)
|
宗教重要性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非常重要 |
95.7 |
30.8 |
90.6 |
72.4 |
|
有些重要 |
4.3 |
26.2 |
6.0 |
10.3 |
|
不太重要 |
.0 |
43.1 |
1.7 |
13.8 |
|
完全不重要 |
.0 |
.0 |
1.7 |
1.3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两个省的两个地区之间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杭州和莆田的教徒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的比例分别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分别为95.7%和90.6%。而在宁波认为不太重要的教徒比例最高,为43.1%。这种差距反映了地区之间的佛教徒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差异。
表30:宗教重要性与职业(n=292)
|
宗教的重要性 |
职业 |
||||||||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公务员 |
私营雇员 |
私营管理 |
教师 |
学生 |
其他 |
|
|
非常重要 |
76.6 |
70.0 |
.0 |
53.3 |
44.4 |
66.7 |
50.0 |
81.2 |
88.5 |
|
有些重要 |
10.6 |
20.0 |
.0 |
.0 |
22.2 |
33.3 |
27.8 |
8.9 |
3.8 |
|
不太重要 |
12.8 |
10.0 |
100.0 |
46.7 |
33.3 |
.0 |
22.2 |
6.9 |
6.4 |
|
完全不重要 |
.0 |
.0 |
.0 |
.0 |
.0 |
.0 |
.0 |
3.0 |
1.3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 |
从职业的角度看,意见较为分歧,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的和有些重要的教徒主要职业是工人、农民、私营雇员、私营管理人员、教师、学生等,但在军人教徒的眼中,100%认为宗教不太重要,公务员教徒的两种看法较为相当,认为非常重要的占53.3%,而认为不太重要的也占到了46.7%。这种分歧的产生的原因在于职业的要求以及教徒自身的素质。
表31:宗教重要性与婚姻状况
|
宗教的重要性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未婚 |
再婚 |
|
|
非常重要 |
77.9 |
78.0 |
20.0 |
|
有些重要 |
4.7 |
12.4 |
20.0 |
|
不太重要 |
17.4 |
8.1 |
60.0 |
|
完全不重要 |
.0 |
1.6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从佛教徒的婚姻状况出发,我们看到已婚与未婚的教徒认为宗教非常重要和有些重要的比例都比较高,而再婚的教徒对宗教则不是很看重,相当多的再婚教徒(60%)认为宗教不太重要。
2.果报观念与社会行为
在佛教中,造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近似于基督教所谓的“原罪”。正是因为人每天都在不停地造业,因此教徒必须时刻修持,以获得精神净化境界的提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种造业的观念在佛教徒中普遍存在,82.6%的教徒都感觉到自己每天都有意无意的造业,而平常没有这种感觉的教徒也占到了17.4%。说明教徒在日常生活中的负罪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佛教的业感缘起及其果报观念对于佛教徒的社会行为是有戒惧作用的。
佛教倡导多做善事,这正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俗语相应。在教徒中,有这种感觉的教徒占72.6%,有些感觉的占16.1%,而没有感觉的占8.2%,说明广大佛教徒对于这种因果报应的道德教化功能还是具有相当深刻的体认的。
当然,这种体认的深刻程度业因佛教徒的地区不同、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
表32:果报观念认同度报与调查地点(n=292)
|
是否感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感觉到 |
88.5 |
31.1 |
86.8 |
71.4 |
|
有点感觉 |
9.8 |
36.1 |
8.8 |
16.1 |
|
没有感觉 |
.0 |
31.1 |
1.8 |
5.4 |
|
其他 |
1.6 |
1.6 |
2.6 |
7.1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认同感在杭州和莆田的教徒中都比较强烈,比例达到了80%以上,而各自与同一省的宁波和厦门相比,后者的教徒的感觉的强烈程度明显较弱。尤其是宁波,有这种感觉的教徒的比例更小,相反的是,宁波教徒没有这种感觉的比例非常高,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地方。
表33:果报观念认同度与职业(n=279)
|
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感觉 |
职业 |
||||||||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公务员 |
私营雇员 |
私营管理 |
教师 |
学生 |
其他 |
|
|
感觉到 |
75.0 |
58.8 |
.0 |
50.0 |
66.7 |
66.7 |
52.9 |
78.0 |
83.8 |
|
有点感觉 |
23.6 |
55.3 |
.0 |
7.1 |
11.1 |
33.3 |
29.4 |
13.0 |
13.5 |
|
没有感觉 |
6.8 |
5.9 |
100.0 |
42.9 |
22.2 |
.0 |
17.6 |
5.0 |
.0 |
|
其他 |
4.5 |
.0 |
.0 |
.0 |
.0 |
.0 |
.0 |
4.0 |
2.7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看,工人、农民、私营雇员、私营管理人员、教师以及学生教徒感到和有所感觉的比例都非常高,他们是非常认同这一佛教道德原则及其社会功能的。而军人教徒对此则完全没有感觉(100%),另外,公务员没有感觉的比例也非常高,达到42.9%。这可能涉及到教徒本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验。总体上看,各种职业的佛教徒对此大都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对于其社会行为应该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精神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宗教戒惧感。
表34:果报观念认同度与婚姻状况(n=266)
|
是否感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未婚 |
再婚 |
|
|
感觉到 |
68.0 |
77.3 |
30.0 |
|
有些感觉 |
17.3 |
13.3 |
30.0 |
|
没有感觉 |
13.3 |
5.0 |
40.0 |
|
其他 |
1.3 |
4.4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婚姻状况的不同,也将影响到对此佛教道德原则的认同。已婚教徒能够感觉到的比例较高,而未婚教徒的认同度比例最高,没有认同的比例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再婚教徒认同感的比例与已婚、未婚的产生明显的差异,没有感觉的比例高达40%。
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佛家道德之中的“三世因果报应”的看法。这种思想作为一种有效的道德律条,对于教徒以及普通大众的社会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调查中,我们发现77.9%的教徒对于三世因果报应的原则具有认同,而5.7%的教徒并无认同,偶有认同的教徒,比例为14.7%。
对此能否认同,也与教徒所在的地区、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关系。
表35:因果观念认同度与调查地点(n=299)
|
是否感觉到三世因果报应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有 |
93.9 |
32.3 |
93.0 |
78.6 |
|
没有 |
1.5 |
9.7 |
1.7 |
14.3 |
|
有时感觉有 |
4.5 |
56.5 |
2.6 |
5.4 |
|
其他 |
.0 |
1.6 |
2.6 |
1.8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杭州和莆田的教徒对于“三世因果报应”有认同的比例非常高,达到了90%以上,厦门的教徒有认同感的比例处于中间,宁波的教徒对这一宗教观念的感觉程度非常低,有感觉的比例为32.3%,为四个地区最底,而没有感觉的比例为9.7%,是四个地区中最高,同时,宁波的教徒有时比例最高,为56.5%。这只能归因与佛教在地区间影响的差异。
表36:三世因果报应与职业(n=189)
|
对三世因果报应的感觉 |
职业 |
||||||||
|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公务员 |
私营雇员 |
私营管理 |
教师 |
学生 |
其他 |
|
有 |
72.7 |
75.0 |
.0 |
50.0 |
33.3 |
66.7 |
58.8 |
87.6 |
90.8 |
|
没有 |
6.8 |
6.3 |
.0 |
7.1 |
22.2 |
.0 |
.0 |
4.8 |
3.9 |
|
有时感觉有 |
18.2 |
18.8 |
100.0 |
42.9 |
44.4 |
33.3 |
41.2 |
4.8 |
5.3 |
|
其他 |
2.3 |
.0 |
.0 |
.0 |
.0 |
.0 |
.0 |
2.9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各个职业的教徒感觉“三世因果报应”的比例基本上都比较高,但是私营雇员教徒的感觉的比例比较低,仅为33.3%,而感觉没有的比例为22.2%,是所有职业中比例最高的,但其有时感觉有的比例也非常高,因此从总体上看,无论何种职业,广大教徒对于这种宗教感觉都比较深。
表37:三世因果报应与文化程度(n=286)
|
是否感到三世因果报应 |
文化程度 |
|||||
|
没读过书 |
小学 |
中学 |
大中专 |
大学 |
研究生 |
|
|
有 |
100.0 |
90.0 |
80.2 |
73.6 |
75.0 |
68.8 |
|
没有 |
.0 |
3.3 |
5.8 |
1.1 |
10.7 |
25.0 |
|
有时感觉有 |
.0 |
6.7 |
12.4 |
23.0 |
10.7 |
6.3 |
|
其他 |
.0 |
.0 |
1.7 |
2.3 |
3.6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三世因果报应的观念与文化程度呈现负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对于这一宗教观念的感觉到的教徒的比例也就越少。没读过书的教徒最能够认同到这一佛教理念,而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徒的认同比例则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在偶有认同感的教徒比例中,大中专文化的教徒比例也比较高,为23%。这组数据说明,作为佛教基本教义原则的三世果报观念对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有一个距离,特别是它的理性化与世俗化的关系问题。
表38:三世因果报应与婚姻状况(n=277)
|
是否感觉三世因果报应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未婚 |
再婚 |
|
|
有 |
74.1 |
81.7 |
30.0 |
|
没有 |
2.5 |
7.0 |
10.0 |
|
有时感觉有 |
23.5 |
8.6 |
60.0 |
|
其他 |
.0 |
2.7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可以看到,能否认同三世因果报应,与教徒的婚姻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未婚教徒感觉到的比例最高,而再婚的教徒有时感觉到的比例最高。说明婚姻经历会对教徒的宗教观念产生明显的影响。
从佛教的基本教义来说,并不是要求佛教信徒直接地将此类佛教认同与其社会、道德行为相互贯通,而是在一定程度的认同基础之上把自己的社会道德行为相应的结合,能够将宗教原则的工具主义方法直接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的期待和希望,并且转化成为一种社会道德观念,产生相互制约的社会效应。然而,我们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各类职业、不同生活经历的佛教徒对于基本的佛教教义及其原则,各自具有不同的认同角度、佛教意识的深浅也出现相应的差异。所以,作为佛教信徒,他们的宗教认同没有问题,但是在具体佛教原则的认同之上,这些佛教信徒则呈现差异,从而说明了信徒们的宗教认同大抵上是私人性强而社会性弱、个人性突出而团体功能淡出。如果要将佛教的基本道德原则由信徒个人的道德惩戒作用,经由人与人的关系协调,最终成为社会道德原则的一个构成部分,其间尚有许多的环节需要沟通。至少就目前的现状来说,信徒们追求的大都是个体的精神安定或者是自我约束而已。
3.精神体验
人们信仰佛教,大多数信徒是希望能够借助于佛教的精神力量来解决自己生活中或精神之中的某些问题。如何感受这种佛教精神,也是考察佛教社会关怀形式的重要方面。在调查中,有65.4%的教徒能够感到佛教的精神能够安定自己,而觉得佛陀、菩萨的精神能够偶尔保佑自己的教徒比例为11.5%,没有感觉的则占3.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佛教精神毫无感觉的教徒也占到了11.9%的比例。
下面是一些具体的调研数据:
表39:感觉菩萨在保佑与调查地点(n=295)
|
是否感觉到菩萨保佑自己 |
调查地点 |
|||
|
杭州 |
宁波 |
莆田 |
厦门 |
|
|
时刻保佑 |
90.8 |
34.4 |
73.7 |
52.7 |
|
有时保佑 |
6.2 |
27.9 |
5.3 |
12.7 |
|
不太保佑 |
.0 |
14.8 |
0.9 |
1.8 |
|
没有感觉 |
.0 |
21.3 |
10.5 |
18.2 |
|
其他 |
3.1 |
1.6 |
9.6 |
14.5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表中显示的是不同地区之间这种感觉的差异,在四个地区中,杭州地区的教徒有这种感觉的比例最高,而宁波的教徒有这种感觉的比例最低,而莆田与厦门的教徒高于宁波而低于杭州的教徒比例。除此以外,宁波的教徒中感觉较低或没有感觉的比例最高,甚至存有怀疑程度。
表40:感觉菩萨保佑与年龄(n=286)
|
是否感觉
菩萨保佑 |
年龄 |
||||
|
17岁以下 |
18—35岁 |
36—50岁 |
51—60岁 |
61岁以上 |
|
|
时刻保佑
|
50.0 |
62.3 |
58.1 |
75.0 |
85.7 |
|
有时保佑
|
12.5 |
12.6 |
9.7 |
10.7 |
7.1 |
|
不太保佑 |
.0 |
2.6 |
19.4 |
.0 |
.0 |
|
没有感觉 |
25.0 |
13.6 |
12.9 |
7.1 |
3.6 |
|
其他 |
12.5 |
8.9 |
.0 |
7.1 |
3.6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从表中看,除了36—50岁的教徒感觉菩萨保佑的比例比较低以外,信徒们的感受基本上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可以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产生某种心理暗示,而这种暗示对于老年教徒则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界于36—50岁之间的教徒,他们正处于由中年向老年过度的时期,因此,他们的心理感觉较为复杂,反映在他们的有菩萨保佑感觉的教徒比例比较低,而精神感觉不太稳定的比例也比较高。
表41:感觉菩萨保佑与职业(n=281)
|
感觉菩萨保佑 |
职业 |
||||||||
|
工人 |
农民 |
军人 |
公务员 |
私营雇员 |
私营管理 |
教师 |
学生 |
其他 |
|
|
时刻保佑 |
76.1 |
73.7 |
.0 |
40.0 |
44.4 |
66.7 |
50.0 |
68.3 |
71.4 |
|
有时保佑 |
13.0 |
10.5 |
50.0 |
13.3 |
11.1 |
33.3 |
18.8 |
8.9 |
10.0 |
|
不太保佑 |
2.2 |
5.3 |
.0 |
13.3 |
22.2 |
.0 |
12.5 |
2.0 |
.0 |
|
没有感觉 |
4.3 |
5.3 |
50.0 |
33.3 |
22.2 |
.0 |
18.8 |
15.8 |
2.9 |
|
其他 |
4.3 |
5.3 |
.0 |
.0 |
.0 |
.0 |
5.0 |
5.0 |
15.7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工人、农民、学生以及私营管理人员等职业佛教徒对此感受的比例较高,总体上在70%左右。感觉菩萨有时保佑的教徒,在军人和私营管理人员中比例较高,分别为50%和33.3%。感觉菩萨不太保佑的教徒中,在私营雇员和公务员中比例比较高,为22.2%和13.3%。而没有感觉的比例在军人和公务员教徒的比例中都比较高。综上所述,仍有相当一部分的教徒对于佛教精神感受较低,不同的职业之间存在不同的情况,尤其是军人、公务员、私营雇员甚至包括教师等,也许他们对待宗教精神的象征作用比较理性。
表42:感觉菩萨保佑与文化程度(n=282)
|
是否感觉菩萨保佑 |
文化程度 |
|||||
|
没读过书 |
小学 |
中学 |
大中专 |
大学 |
研究生 |
|
|
时刻保佑 |
100.0 |
90.0 |
64.4 |
62.8 |
66.7 |
25.0 |
|
有时保佑 |
.0 |
6.7 |
11.0 |
11.6 |
18.5 |
18.8 |
|
不太保佑 |
.0 |
.0 |
2.5 |
7.0 |
.0 |
6.3 |
|
没有感觉 |
.0 |
3.3 |
11.0 |
14.0 |
7.4 |
31.3 |
|
其他 |
.0 |
.0 |
11.1 |
4.7 |
7.4 |
18.8 |
|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此表说明,在各文化层次之中,能够感觉菩萨精神的教徒比例基本上随着文化程度的的上升而逐渐下降,无文化的信徒感受度为100%,而有研究生学历的仅为25.0%。其他各种感受,基本上又按照这种变化趋势,说明年轻而又文化程度较低的教徒,其精神感受更具宗教象征意义。
表43:感觉菩萨保佑与婚姻状况(n=269)
|
是否感觉菩萨保佑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未婚 |
再婚 |
|
|
时刻保佑 |
70.7 |
63.8 |
20.0 |
|
有时保佑 |
9.8 |
12.4 |
10.0 |
|
不太保佑 |
6.0 |
1.7 |
30.0 |
|
没有感觉 |
11.0 |
11.3 |
40.0 |
|
其他 |
2.4 |
10.7 |
.0 |
|
|
100.0 |
100.0 |
100.0 |
相信菩萨保佑的感觉,在已婚教徒中,感觉到菩萨保佑的比例非常高,未婚教徒的比例居中,再婚教徒的比例最低,只有20%,而再婚教徒没有这种感觉的比例高达40%。说明,再婚教徒对于菩萨精神的感受持有很大的怀疑。
调查中所反映的情况是,教徒的精神感觉大都一致,但是在精神感受的具体结果上,则存在着明显的认识的不同。从调查中来看,35.9%的教徒认为菩萨信仰能给自己带来信心,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其他感受,依次是菩萨信仰能够带来身体健康(23.9%)、事业成功(12.2%)、生活富裕(8.8%)等等生活目标。当然,更多的教徒认为这种信念,可以带给自己的主要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
精神的体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作用,既可以作为象征所具有的形象再现宗教的或道德的力量,亦可以从此类宗教象征之中分离出相应的思想符号,并能够以此再现符号所具有的思想力量。从此层面而言,佛教更为注重个人的精神觉悟,能否觉悟关键是在于个人的领悟的深浅而已,从而也是加强了现代佛教信徒的个人特征,促使其精神体验更具个体性、私人性。
若干问题的讨论
通过对四个地区的佛教徒所进行的调查,我们发现,这四个地区的教徒在以下一些方面存在如下特点:
首先,由于在样本中的年龄构成相对较轻,因此信仰佛教的时间都比较短,最多的是在10年以下(62.3%)。在佛教徒中,领过皈依证的占80.1%,而没有领过皈依证的仍然占到了19.9%。说明相当一部分佛教徒还没有意识到皈依证的获取,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转变,更是要在社会行为上对于佛教僧团具有一种认同和依属的感觉。
教徒们最初接触佛教的原因主要是“寻求解脱和觉悟”(62.3%),作为教徒接触佛教的主要途径,看佛经(39.9%)对于人们入教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信仰佛教之前,人们精神求助所采用的各种方式中,最为普遍的对象是“各种宗教书籍”(52.5%)。
其次,信徒们的宗教活动大致已经从寺院转入家庭,已经有了相当程度上的家庭化。去寺院拜佛的教徒在时间的安排上比较分散,经常坚持去寺院拜佛的教徒并不多,更多的教徒是需要去的时候才去(20.7%)。同时,很大一部分教徒是选择某个特殊的日子才去寺院礼佛,或者是佛教节日去(17.4%),或者是初一十五去(14.4%),或者是每年春节去(9.2%),69.3%的教徒家中设有佛龛,而82.4%的教徒经常在家中拜佛。家中佛龛的出现与发展,家庭的宗教功能在加强,逐步取代了佛教寺院在经常性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另有很大一部分的(77.5%)教徒在平时阅读佛经,不读佛经的教徒仅占1.9%,只有18.4%的教徒偶尔读佛经。
宗教与现代人的关系,教徒已经有很明确的认识。75.7%的教徒认为非常重要,10.7%的教徒认为有些重要,只有12.3%的教徒认为不太重要,而认为完全不重要的教徒更少,只占调查样本总体的1.3%。佛教道德原则的戒惧作用,在佛教徒中已经普遍存在。82.6%的教徒都感觉到自己每天都有意无意的造业,而平常没有这种感觉的教徒也占到了17.4%。在因果报应观念方面,77.9%的教徒对此认同,而5.7%的教徒并没无认同,偶尔认同的教徒比例是14.7%。
祈求佛陀、菩萨保佑是教徒的一种精神寄托。在调查中,65.4%的教徒感到菩萨在时刻保护自己,觉得有时能够获得菩萨保佑的教徒比例为11.5%,感觉菩萨不太能够保佑自己的占3.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这种精神认同的教徒也占到了11.9%。
总之,从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佛教在杭州和莆田的历史影响比较深厚,无论从皈依情况、宗教活动、宗教信仰以及精神体验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宗教态度都非常虔诚,所接受的佛教传统的影响也比较深刻而具体。
其次,与我们的调研状况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该地区的佛教信仰现象,说明了当代中国佛教与社会变迁的特殊关系。最为突出的并使人关注的是——佛教信仰的私人化、个人化价值倾向。尽管中国的宗教传统曾经有“制度型”与“扩散型”的矛盾,而扩散型是中国宗教的的首要形态,宗教成分渗透于中国社会制度内及其社会生活之中,导致“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会特征。
(yang.c.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y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而传统的佛教历来注重个人的修行和修养,寺院作为宗教团体的作用并不是十分突出和重要,但是,佛教寺院及其僧团对于信徒者个人的制约作用,还是通过皈依的师徒关系、群体性的佛教礼仪的施行等等而得以体现。然而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佛教信徒则少去或者不去寺院、即使去寺院也无活动规则。他们的信仰形式、精神体验、对于佛教道德原则的感受等更为个人化,几乎成为了宗教性的个体行为。
除了佛教传统的历史影响之外,我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个现实社会变迁的潜在作用,这就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促使社会领域发生的深刻的分化,那就是由一个总体化的计划经济社会向着多元的、多层次的社会演变,社会领域已经初步分化出政治领域、经济市场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初步具备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而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领域的分化或分割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前提,正如下图所示:

行政
警察
司法
国家领域
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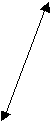 政府机构
秘密警察
政府机构
秘密警察
 间谍
间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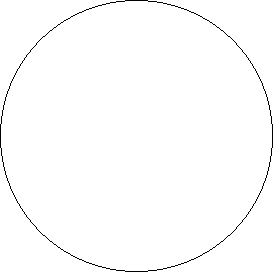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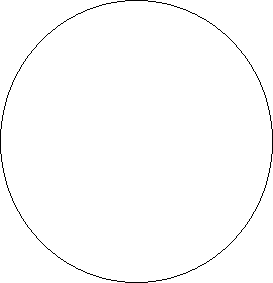 公共福利
公共福利
政党
媒体,教育
国防承包
规章
及科研
*
私营媒体,
工会联合会
![]() 公共领域
教育,医疗
市场领域
公共领域
教育,医疗
市场领域
志愿社团:
保健
雇主联合会
企业 工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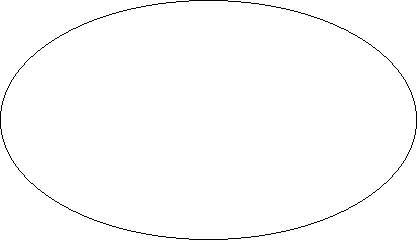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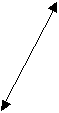 福利,公益,
市场
福利,公益,
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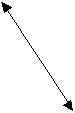 宗教
社会运动
消费者协会
宗教
社会运动
消费者协会
自助团体
媒体和法庭
家庭企业及精
中透露的私
英俱乐部网
人生活
家庭 爱情
亲友
私人领域
性关系
这是一个定位于文明社会的公众和私人各领域的示意图([美]托马斯·雅诺斯基著,《公民与文
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页)。它表明了各个领域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地位及其功能。在这个示意图之中,作为社会团体之一的宗教组织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而作为个人信仰的现象则存在于私人领域。在这两者之间,可以紧密联系,也会出现分化。依据本课题所做的研究,这种分化的现象比较突出,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已经伴随着社会变迁或者说是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之一而渐渐呈现,特别是个人的认信过程的出现、宗教生活的时间、地点、方式的个人化等,均可以是作为这种社会的、宗教的现象。
这说明,“与传统社会秩序相比较,现在基本公共制度不再深入地影响个人意识与个性的形成,尽管这些制度的功能上合理的‘机制’对人们施加了大量行为控制。个人认同基本上成为一种私人现象。也许,这是现代社会最具革命性的品质。制度分割给个人生活留下了未加组织的广大领域,也给个人经历的中心意义脉络留下了尚未决定的广大区域。从来自制度分割的社会结构间隙中的出现了所谓‘私人领域’。”(托马斯·卢克曼著《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108页。)而出自这个“私人领域”的信仰选择或宗教活动方式,那就是宗教的私人化现象的出现。这一现象出现在佛教领域,就是“个人佛教信仰”与“僧团性寺院佛教”的一定分离。佛教的信仰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了私人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调研当中,几乎所有的指标都没有达成一致的认同,即使是自可以出现一致的佛教礼仪层面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一旦宗教被定义为‘私人事务’,个人就有可能从‘终极’意义的聚集中挑选他认为合适的东西—只听从有他的社会经历所决定的偏好的引导。”(托马斯·卢克曼著《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第109—110页。)
个人的社会经历、社会习惯以及生活际遇等等因素,左右、制约着信徒们的宗教偏好。
因此,个人宗教性问题的出现,乃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现象。它既是个人价值观的相对自由空间,又是私人领域合法性空间的一个表征。但是,它与制度化、组织化的宗教性的相互渗透及其相互嵌入的问题如何,构成了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社会特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常“私人化”、“个人化”的佛教徒,在面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的问题上,如道德危机(37%)、精神空虚(26.8%)、环境污染(17.6%)、战争暴力(12.9%),等等,他们依然认同于佛教的社会功能。他们依然认为佛教能够重建社会道德(22.1%)、使人类互相友爱(21.7%)、建设精神文明(16.0%),可以满足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渴望。同时,他们社会生活中的理想目标,也皆与佛教紧密联系,如12.2%的教徒相信佛教能够拯救人类,佛教可以为人类提供安全感与精神慰籍,还有10.2%的信徒寄希望于佛教的社会功能能够消除战争(10.2%)等等。可见,私人化的佛教信仰之中依然还包含着内容丰富的社会道德内涵。问题是,这些佛教信徒的社会行为如何在其私人领域之中自由地作用出来。
文明社会一般分化出来的四个领域——私人领域、公众领域、市场领域和国家领域,各个领域之间相互重叠贯通。其中,公众领域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但也是一个最难说清楚的领域。至少有五种支援联合组织活动于这一领域,如政党、利益集团、福利协会、社会运动和宗教团体。然而,宗教团体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它们的活动通常都是在私人领域,例外的情形则是它们企图通过志愿活动或公共对话,对整个社会的福利事宜施加影响特别是当它们在自己成员范围之外,还向社会、公众提供某种公益服务或政策建议的时候,其作用就更是如此。(参托马斯·雅诺斯基著《公民与文明社会》,第19页。)在此基础上,寺院僧团佛教的社会功能及其体现的形式,也许会由此发生应有的变化。否则,讨论佛教的社会功能,很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