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鄙人从事禅学研习有年矣,虽偶有作品问世,然如同大草原上的野花,星星点点,夹杂在草丛之中,很不起眼,它也如同我这生活在夹缝中的人一样无人知晓。然而,尽管鄙人的文字不起眼,但还是具有某些参考作用的。鄙人清楚地记得自己从事沩仰宗禅的研习是在1995年春,成果分别在95年的《正法眼》、《内明》、《船山学刊》等处发表过。可后来也有“正宗”的学者做了这方面的研究,结集在《禅宗宗派源流》一书中,由于本人不起眼,居然有人对鄙人的沩仰宗研究成果也产生了怀疑。鄙人在不得而已的情况下,只好亮出原来发表的成果,比《禅宗宗派源流》一书早了近5年,是谁参考了谁的成果,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自然,像这样不负责任的批评、甚至不惜采用盗憎主人的做法,鄙人所遇到的并不多,但任意摘引本人的文字而不注明出处者就较多了。尽管本人从不愿意“盗版”人家的东西,宁可自己辛辛苦苦地去耙梳原始材料写来,哪怕是写得极朴质、极笨拙,到底也是“家做货”呀!文章发表出来,本来是给人看的,因而有人参考,本身应该是一件好事。但现代社会注重“知识产权”,鄙人不是名人,因此发表了成果很难不被人怀疑是“盗版”,这大概也是社会认识中的一种难以改变的惯性吧。
近年来,网络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也偶尔有一些网站转载鄙人的作品,例如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网、凤凰网、佛教在线、台湾大学的狮子吼网站等十多个地方,均刊载过鄙人的作品。甚至连浙江金华日报的书画版,也把鄙人《禅之艺术》一书的书法章节的个别文字转载出来了,他们确实是对鄙人钟爱有加。尽管这些网络的编者对鄙人的文字存有怜惜之情,但他们在转载鄙人的作品时,却从未打过招呼,只有当鄙人在用www.google.com搜索时,才对这些大德的美意有所发现,这些无疑也是一种遗憾。
大约在四年前,台湾现代禅网站的学者温金柯先生提出要发表鄙人的作品,鄙人颇为感激,由是有十多篇文字相继在那里发表。然世法无常,现代禅的创始人李元松大德不久辞世,由是这一都市中的丛林从此也就消失了。去年,鄙人应邀去苏州西园寺的研究所讲座,遇上一位名叫廖乐根的研究生,他很热情地提出给鄙人刊一个文集,由是鄙人在现代禅文集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文字,做成了一个文集刊登,以供广大读者批评。随后,鄙人又去杭州开会,遇上了方外交刚晓法师,他很热情,提出帮鄙人在网站上刊登文字,并提议鄙人将论文之外的小品文字结集,其诚实在感铭肺腑。因此,鄙人又冒昧地借“灵山海会”的空间再度献丑啦!
提起刚晓法师,不少对他缺乏了解的人总是误认为他喜欢“走偏锋”,认为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有些偏激。其实,这种看法也不足为怪,在鄙人与刚晓法师刚相识时也曾有过。但经过与法师长久的交往,鄙人发现在刚晓法师那貌似“偏激”的骨子里,却包藏了一颗正直、善良的道心,他的那种护法的诚心,正是采用这种“偏激“的方式来表现的。然而,人们在解读法师时,却往往忽视了他的另一面,殊不知他就像韩昌黎的《送董邵南序》那篇奇文一样,是貌偏而实正的一位法师。自然,法师那超凡的智慧,他对玄奘法师著作研究的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更是令鄙人钦佩不已。
有感于斯,拉杂凑了这些句子,聊以作为这个文集的卷首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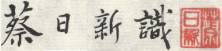
时公元二○○四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