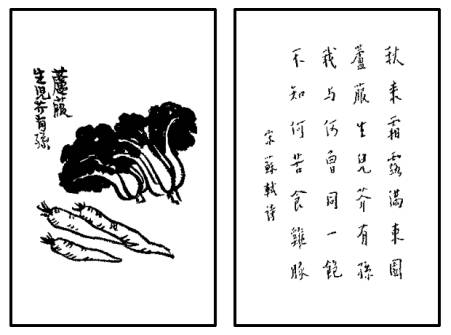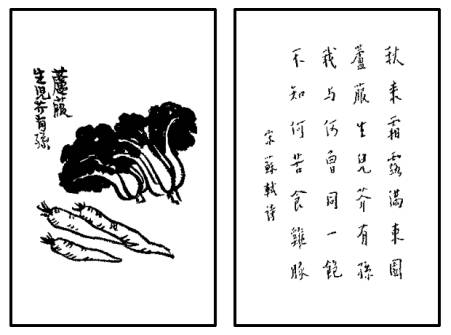
放生的隨想
大癡
每年的生日,我都有一個成例,那就是放生。
對此,我是這樣想的:上蒼尚且有好生之德,何況佛陀的慈悲更以利樂一切有情爲鵠的,我的生命能延續至今,不僅要感謝上蒼的好生之德,更要感謝佛陀的慈悲。因此,每當我年齒增長的紀念日到來,便自然地想起了以放生的方式來報恩。
提起放生,本人對此頗有些感想。原先,我曾隨同教內的信衆參加過多次放生活動,那確實是培養大衆慈悲情懷的一種有益活動。在參與了幾次這樣的活動之後,我對此也另有一些想法:這樣的活動固然是好,但似乎仍然局限在有爲的功德中,並且也過於拘泥形式。
首先,放生的時間一般多定在佛誕或觀音等菩薩的紀念日,但在此前,信衆們早在募集資金購買各種動物。那些原本是經過了人爲捕獵傷害了的動物,放在信衆的家裏蓄養一段時間之後,不但沒有恢復元氣,而且越發與它們所生存的大自然疏遠了。等到將這些生存能力不強的動物放回大自然之後,它們中的存活率究竟能有多少,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質疑了。
其次,江南的寺院大多有放生池,放養在池中的水族雖然享有聽聞佛法之便,他們伴隨晨鍾暮鼓的生活自然也饒多法喜。但放生池畢竟是一塊有限的空間,且不同的水族動物的食物選擇也不同,它們未必能獲得充足的食品來維持其生命的延續。加上有的水族動物是肉食類的,它們一時是無法改變其食物習性的,因而在放生池中又不免會弱肉強食起來了。在杭州淨慈寺的放生池中放養了不少的龜類動物,它們往往因缺少食物來源而形體羸瘦不堪、其生命似乎難以延續。假如人們將肉食投入放生池中,又大違護生的情懷;如果不這樣做,那麽多的烏龜必然會活活餓死在放生池中。又如蘇州西園寺中的放生池,其規模比一般寺院的要大得多,在池中還放養了兩隻三百年的大黿。就由於有了它倆,池中的其他水族時常遭到捕殺,有一次信衆在池中放養了兩隻鴨子,也給大黿吞吃了。寺中的一位老師傅對此很生氣,他傍晚時坐在池旁的石欄上大罵這兩頭癩頭黿,話語中充滿了對這兩個不爭氣的傢夥的歎惋。癩頭黿儘管長期在寺中聆聽法音,但由於它們的業力太重,還是無法改變其殺生的習慣,可見定業難轉呀!在此,我不禁想起了洞山禪師的一段開示:當時有學人問洞山“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洞山禪師當即開示他說:“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像這樣不觸不背、既不違背自然的生態的法則,又嚴格遵循佛教慈悲精神的開示,非洞山老人,別人實在是難得道出。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果真有那樣一種慈悲精神,放生又何苦一定要選擇在吉祥的日子呢?又何苦一定要拘泥於那種宗教形式呢?只要我們具有這樣一種慈悲情懷,遇上了可以解救的動物,便可隨緣施以無畏,不必拘泥於有相的形式,那該多好啊!這樣,不但動物獲得了及時的救助,而且它們回歸大自然的存活幾率也要大得多。
然而,走筆至此,本人似意猶未盡。那就是我們在放生的同時,往往會既不情願但又無可奈何地遇見了傷生、殺生的現象。我的生日是在萬物復蘇的春天,也是各種動物繁衍的季節,可每當我到江邊投放水族之時,那些電漁的船隻怎是出現在我的眼簾,令我不得不陷入了沈思。在經濟建設日益繁榮的今天,生態與人文的破壞正在日益加劇,人類在取得經濟建設成果的同時,卻又失去了那些極爲寶貴的東西,這難道不夠發人深思的了麽!
在另一方面,“放生”固然重要,但與“放生”相比,“護生”似乎顯得尤爲重要。在上個世紀,藝術大師豐子愷用他傳神的畫筆描繪了四部《護生畫冊》,對當時社會的教化有著不可估量的積極意義。然而,如今隨著經濟建設的日益發展,人們護生的理念卻漸漸地淡薄了,尤其在南方經濟發達的省份,那裏的人們競相食用野生動物,乃至造成了去年的“SARS”
席捲全球,給各地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並奪走了數百人的生命。面對這種社會現象,我們在舉辦放生活動以培養人們慈悲情懷的同時,極力提倡護生,積極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慣,大力提倡素食,無疑是更爲重要的措施了。因爲,只有這樣做,才能從源頭上斷絕人們的“殺生”:由於大家都不吃葷腥了,那麽,那些依靠捕獵爲生計的人們便會失業,這樣自然生態便會恢復平衡。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更多的人們認同佛教的這一慈悲精神,自然也有待於佛學的日益普及了。在《護生畫冊》的第一集中,有一幅題爲《蘆菔生兒芥有孫》的作品,並附有弘一大師手書的蘇軾詩作,謹將此詩鈔來作爲通篇的小結。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